村长母亲的葬礼
发布时间:2019-11-15 09:07:22作者:心经入门网村长母亲的葬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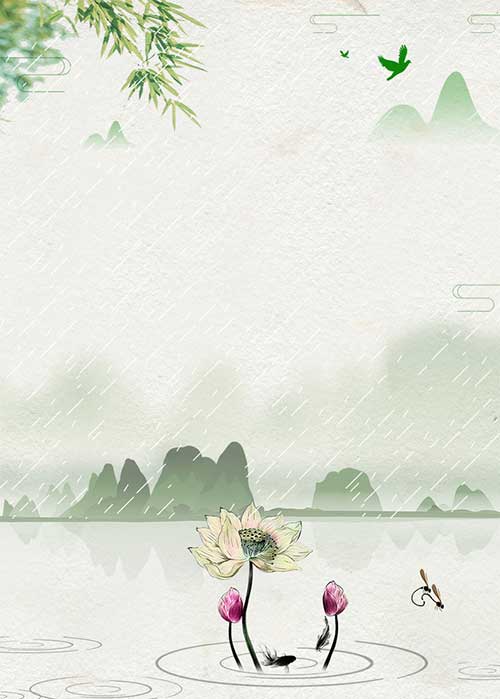
村长的母亲驾鹤西去了,时值三九寒冬,享年73岁。老人家坎坷一生,终究没有跳出古人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叫自己去。”的周期律。
村中负责红白理事的人与村长相商,说:“老人家无疾而终,实属罕见!按说是喜丧,应大操大办。可村长是公家人,怕有损于您的前程,丧事是否从简呢?”
村长一听,脸上阴沉沉的,说:“老娘一生坎坷,晚年我待她不薄,又无疾而终,理应走得风光一点,就按喜丧办吧。天塌下来我顶着!”
丧事负责人听后,心想:村长是一村之主,又是一家之主,别拿村长不当干部。我这不是“咸吃萝卜淡操心”吗。于是,他便请来了县里的京剧团、方圆几十里闻名的吹鼓手……”
出殡那天,天气贼冷。大清早,哭叫声悲悲切切,喇叭声呜呜咽咽,在村子上空游荡,令村人听了好不伤心。不多时,大街小巷停满了吊唁人开来的车子。花圈也从村长家摆到了大街上。
大街上车水马龙,络绎不绝。东庄赵村长来了,村长率孝子贤孙出门叩首相迎;西庄钱村长辞灵后走了, 村长率孝子贤孙跪拜相送……村长着一身孝服低头哈腰,目不斜视,迎来送往,忙得要死,俨然孙子一般。
村长忙,外柜先生更忙。
村长家大门口旁,8张桌子一字排开,每张桌子上坐着两位外柜先生。只见记账的奋笔疾书,不舍抬头;收受祭品和赙资的手忙脚乱,钱不离手,边点边喊:孙村长赙资500元! 李村长赙资1000元……瞬间功夫,花花绿绿的票子小山似地堆满了桌子,众人惊得目瞪口呆。

午时临近,亲朋好友该来的,都到了;不该到的,也都来了。可奇怪的是村长姥姥家人未来。直等到午时已过,也没见到村长姥姥家的人影。按习俗,村长姥姥家的人未到,丧主家是万万不敢下葬的。村长已率孝子贤孙到村口去了一遍又一遍,就是不见人影。等得帮忙的人意乱心烦。又过了一个时辰,村长姥姥家终于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,有男,有女。女客排队喊冤叫屈地嚎啕着直奔灵柩旁,男客径直来到外柜前登记。
村长姥姥家是“苟”姓,来的人自然姓“苟”了。男客中为首的一位走到外柜先生桌前,打了个招呼。外柜先生文绉绉地问:“请问先生尊姓大名?”男客也很有斯文地答:“敝姓‘苟’,小名苟有礼。”外柜先生听了,持笔的手装模做样在半空中悬了半晌,笔头子也没触到纸上。良久,外柜先生突然抬头问:“敢问先生,您是哪个‘苟’啊?”
男客一听,心想:老东西,你这不是故意戏弄我吗。就不慌不忙地说:“老先生,你就别管那个‘狗’哩,那个狗写上也行。我都没意见。”
外柜先生持笔的手抖了起来,在来人地催促下,最终,笔尖也没触到账簿上。僵持了半天,外柜先生却岔开话题说:“请问先生,您赙资多少啊?”
男客不慌不忙地向口袋里摸了摸,抽手往桌子上轻轻一拍,说:“我赙这钱的一半,请找钱吧!”众人看了,桌子上竟是银光闪闪的一枚1分的硬币!
“怎么来了个疯子呢?”众人没说出口。
不知不觉,起灵的时刻到了。只听主丧人一声呐喊,紧跟着是陶盆摔地的哐当声、孝子贤孙的哭叫声和喇叭的呜咽声交织在一起,从村长家大门口爆发出来。村长母亲的灵柩(骨灰盒)安放在一辆用面包车装扮的龙头花轿里。轿前,8支长长的大喇叭朝天呜咽着开路,每只喇叭上渐次挂满了主人家赏赐的百元大钞。为首的一个吹鼓手最卖力,赏钱得的也最多。吹起来,他两腮鼓得像偷运粮食的搬仓鼠,可没多久就瘫在了半路上。轿后,送葬队伍中哭得最凶的当属村长,哭得死去活来,昏了过去……
这时,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在偷偷议论:“别看村长哭得凶,他这是在唱戏。知道他老娘是怎么死的吗?他娘是生生的被他气死的!”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