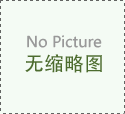传统佛教的文学观——汪娟
发布时间:2024-01-05 01:47:49作者:心经入门网五、结论
以上由汉译佛典、译经家和僧俗雅士三个方面对传统佛教的文学观进行了考察,综合以上的论述,可以进一步推衍以下几点结论:
1。汉译佛典的文学观偏向于“崇实尚用”,文学是为宗教服务的,凡是无益修行的戏论文字皆应舍弃(小乘),凡有助于利益众生的文艺赞咏皆应学习(大乘)。译经家的文学观偏向于“重质轻文”,认为翻译的重点在于保存经论的本旨,语言风格宁可质朴而不要太多的文巧修饰,注重文学的内容远过于文学的形式。僧俗雅士的文学观,主要是从小乘的观点(诗魔、绮语皆为掉悔,应当舍弃)中解放出来而迈向大乘的观点(化掉悔为道机,化诗魔为空王,化绮语为道种),致力于“文道合一”的文学观,因此对文学内容的重视,依然胜过于形式。
2。由于佛教注重文学的实用性,因此举凡佛经的翻译,俗文学中变文、宝卷、劝世诗偈、俚曲小调、灵应小说等,都是为了弘宣佛教的目的而盛极一时。佛教的散文包括论议、碑铭、忏文、愿文……等等不同的文体,也是为了护法弘教而创作的。佛教的诗歌不只是吟咏情志,而且是以诗作佛事,以诗词来悟道的。
3。由于佛教偏重于文学的内容,因此佛经的文体,质朴而近本,不用绮词俪句48[70];佛教的灵应小说,语言质直不文49[71];佛教的诗歌,劝世诗则近于俚俗口语,俾使村夫村妇皆能解;禅门悟道诗则尚乎清丽高逸,以“不立文字”之文字发挥禅理,正所谓“但见情性,不文字,盖诣道之极也”。[72]
传统佛教的文学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,资料也相当琐碎而繁多,原本应依时代顺序、针对相关的作家和作品逐一进行细部的探研,才能得出全面而系统性的成果。由于笔者才疏学浅,囿于时力,只能先以宏观的角度进行探索,至于其他后续的问题,留俟来日进一步地研究。
[1]《大正藏》50,页332中。 [2]《大正藏》51,页881下~882上。 [3]《大正藏》2,页345中。 [4]《大正藏》4,页557下。 [5]《大正藏》7,页597下。 [6]《大正藏》8,页626中。 [7]《大正藏》8,页839中。 [8]《大正藏》44,页669上。 [9]《大正藏》14,页540下。 [10]《大正藏》14,页548上。 [11]《大正藏》10,页192中。 [12]收入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(张曼涛主编,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9,大乘文化出版社),页345~382。 [31]见梁启超,前揭文。 [32]《大正藏》55,页53上~中。 [33]《大正藏》55,页55上。 [34]《大正藏》55,页63下。 [35]《大正藏》55,页71下。 [36]《大正藏》55,页74上。 [37]《大正藏》55,页73上。 [38]《大正藏》55,页76中。 [39]《大正藏》50,页437上~439下。 [40]见梁启超,前揭文。 [41]《大正藏》50,页459中。 [42]《大正藏》50,页724中。 [43]《大正藏》52,页330~331。 [44]收入严可均校辑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第3册(台北:宏业书局,1975.8),页3010上。 [45]《大正藏》53,页829上。 [46]《大正藏》53,页468下。 [47]《大正藏》47,页1062下。 [48]《白氏长庆集》卷16(收入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80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.6),页185。 [49]同前注,卷45,页493~494。 [50]萧丽华,〈晚唐诗僧齐己的诗禅世界〉,《佛学研究中心学报》第2期(1997.7),页157~178。

作者:汪娟